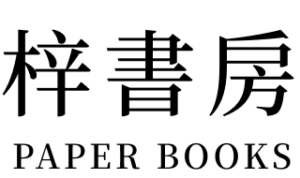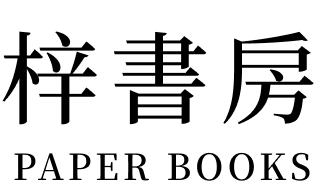時間:2019年11月16日
地點:梓書房
對談:言叔夏X李欣倫
紀錄:梓書房
分享我們的第一本村上春樹
✦欣倫:
我的第一本村上春樹是《聽風的歌》。這本書出版於1979年,那時候我才一歲,叔夏還沒出生,我想在座的各位也都不知道還在哪裡,村上春樹就寫了第一本小說,並且得到群像新人獎,村上春樹在當時得獎是很爭議的一件事情,因為這本小說,並沒有很明顯的故事或敘事的主軸。村上春樹在《身為職業小說家》裡是怎麼說的呢,他開始寫小說的時候,就很有意識的想要寫一個「什麼都沒有」的故事。我們往往覺得一個故事要有高潮迭起,或是特別的設計,可是他說,跟前輩的作家比起來,要怎麼展現他的個別性,就是把他手上僅有一些輕量型的素材,將它拼貼組合在一起:唱片行、音樂、酒吧文化,背景是淡淡的與學運相關的。
.
我大概二十歲左右,讀的時候非常驚訝,因為在高中時代當時讀的小說大多是黃春明、陳映真和王禎和的作品,《聽風的歌》完全是一個不同的世界。《聽風的歌》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它展現了村上獨特的寫法,例如他喜歡用數字,大家抽到七千三百幾十根菸的時候某件事情就發生了;他也喜歡吃冷的東西,很少吃拉麵,但是吃義大利麵,他抽菸、喝啤酒,過這樣的生活,對於初讀小說的我是很特別的經驗。
.
之後我讀了《遇見100%的女孩》,裡面有一篇,在四月裡晴朗早晨遇見了一個100%的女孩,描寫一個年輕人,有一天遇到一個100%的女孩,他不知道怎麼去跟她搭訕,所以決定要跟這個女生講一個故事,從「從前從前」開始,以「妳不覺得很悲哀嗎?」結束。還有一篇〈1963/1982 年的伊帕內瑪姑娘〉我很喜歡,他怎麼形容一個女孩子的美麗呢,他說最美的地方就是她的腳底,簡直是一種形而上的腳底。不知道在講甚麼,我們讀過台灣鄉土文學裡現實的荒腔走板,所以讀村上非常震撼,不管是小說裡面的音樂或是文字,還是他描寫的意象,都有一種朦朧的距離感,好像有點懂可是不太懂。
.
✧叔夏:
我們這個組合好像還蠻適合談村上的,我們這個台灣的六七年級世代,剛好是村上春樹翻譯進台灣的第一批讀者,我們讀的時候剛好就是在座各位的年紀。
.
我的第一本村上春樹國三那年讀《挪威的森林》。我們那個時代最流行的是朱少麟《傷心咖啡店之歌》,就是除了欣倫講的黃春明這個譜系之外,其實在同學間也很流行一個蠻新的傾向,像《傷心咖啡店之歌》這樣非常接近村上作品的東西,他們在一個酒館裡面談論康德黑格爾,但是談論的方式又不是哲學性的,它常常是對應到人的存有,這個東西我覺得它發生在十幾、二十幾歲的讀者身上,是很容易找到共鳴的。
.
按照村上的說法,《挪威的森林》跟之前寫作方式完全不同,他也說不喜歡為小說加後記,可是只有為《挪威》加了一個其實是很感性的後記。他在許多的作品裡面那些抽象的、架空的小說寫作,用一個輕飄飄的空氣去遮掩內在巨大哀傷的部分,但是這個部分在《挪威》小說情節裡,尤其在後記裡卻抓地性很強,他很直接地面對了自己在這本小說寫大學青春的時代,他所遭遇的人跟事。剛剛欣倫有提到《聽風》裡有淡淡的學運背景,《挪威》開篇就是1968年全共鬥開始。
.
《挪威》翻譯到台灣應該是1990年代,我手上的是時報1996年版,台灣讀者對村上春樹的接受,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當中也有思想上的接承,因為台灣也剛經歷過野百合學運,在學運結束之後是一個低伏的時期,我們面對的世界某種程度上是虛無的,你走在城市開始建造的街道上找不到你自己,就像小說鋪建出來的1960-1970年代的日本街道,大學生們在教室的課堂找不到自己,只能往外去找,在街道上白天晃蕩,晚上打工跟女孩睡覺,隔天再爬回宿舍,我覺得它裡面有個非常甜美但是其實是巨大空洞的哀傷。
.
另一本是《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這兩本書其實對我而言,村上都勾勒出一個,對於當時做為一個台灣讀者的我來講,九零年代快結束了,我記得當時有個都市傳說,就是兩千年來之後,有個千禧蟲會在你電腦裡把東西都吃掉。大家對於世界即將要終結之前,那種巨大的空洞,以及我們以後要去哪裡,在這個終結的過程裡面,這兩本書對當時的台灣讀者而言是別有意義的。
.
村上春樹筆下的青少年物語

✦欣倫:
如果大家熟悉村上的作品,會發現他筆下的少女都不會是偶像雜誌包裝的美少女,他的都有點怪。像叔夏談到的《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這本是一個胖女孩,又胖又年輕又很漂亮這是很不容易的事,這個女孩竟然兼具了。村上怎麼形容她的胖呢?像夜裡下起無聲的大雪一樣,就是形容她的脂肪很多。她的頸根飄散著古龍水的香味,好像夏天的早晨站在香瓜田裡的那種香氣,因為沒有辦法理解一棵樹或是一陣雨的感覺,就會很哀傷。在村上的小說裡,你可以感到時代的脈絡,也有他處理很多人深層的孤單和不被理解的感覺。
.
《1Q84》裡的怪女孩深繪里,小說描寫這個女生就是非常美,眼神特別,兩個瞳孔看出去的深度不太一樣,長髮皮膚白皙,講話沒有起伏,不太能夠用一般人的語速還有聲調來理解,村上特別描寫了她的胸部,大的不成比例的乳房。我在讀的時候她的形象就跳到我腦海裡了。
.
另外一本,也是我最喜歡的《國境之南太陽之西》,裡面有個少女叫做島本。駱以軍的小說《降生十二星座》裡有直子,邱妙津的小說,也是不斷提到村上,其實可以從台灣很多小說家裡看到他們對村上春樹小說的喜愛和接受,像是風格或名字的設計。像我因為太喜歡《國境之南》,我的散文集裡有個女生我也叫她島本。
.
其實你在看村上的小說的時候,很難不聽音樂,因為他的小說的文字還有氣氛整個背後都有一種淡淡的背景音在播放的感覺,這是村上作品中蠻大的特點。《國境之南》當中有一段我很喜歡,島本邀請主角阿始到他們家來聽音樂,村上描寫她是怎麼樣放唱盤的,她會小心翼翼地將唱盤從封套裡拿出來,用捧著的,手指都不能刮到凹槽,唱盤上有很多紋路,捧著放上去之後呢,就把唱針放在唱片上開始轉動,音樂就開始播放了,聽完之後她又會很小心的將唱盤拿起來,用除塵劑噴一下,機器也整個擦拭過,整個過程就很像一個儀式。阿始每次在旁邊看島本操作唱片的時候,就深深地被吸引,他們很常聽的其中一首爵士樂是納金高(Nat King Cole),我那時候因為很喜歡村上春樹,所以書裡面談到的樂手,我就去買他們的CD,有一首歌叫做《Pretend》:
.
Pretend you’re happy when you’re blue
It isn’t very hard to do
(當你很憂傷的時候要假裝你很快樂,這不是太難的事情)
這是一首很哀傷的歌,但是納金高唱起來游刃有餘,非常有爵士的風範在裡面,所以這三本都是我很喜歡的小說。
.
✧叔夏:
最近村上有個新聞是,村上把他的手稿捐給早稻田大學,其實他是一個非常少出現在媒體的作家,所以最近我看到新聞有點被嚇到,以前看村上的照片好像都停留在某個時期,可是這次的新聞我突然驚覺他的頭髮已經白了,這個形象對我來講有點震撼,因為他的小說每一本都有非常多的青少年或少女。我覺得他很多的小說裡面的少年都有強烈的他自己的影子,村上常常把握住了青春期的某一種,進入到這個世界,和跟世界斷裂的縫隙。就好像《挪威》裡講原野上面有一口井,不小心就掉進去了,可是成人不會發現這口井的,只有那些細小的在草原上像兔子一樣行動的小孩子,一些十幾歲的孩子們,他們才會在這個草原上一不小心就找到這口井。
.
我想要談的是《海邊的卡夫卡》跟《沒有色彩的多崎作》。村上取名字很有趣,他喜歡把日本的姓氏加上一個翻譯的名字,形成一個強烈的符號感,例如《海邊》的少年叫做田村卡夫卡,在15歲生日做了一個決定要離家出走,到遙遠的地方去。小說開始就寫了他跟烏鴉的對話,烏鴉當然是抽象的存在,烏鴉跟他說你只有變強壯,你才可能真的在離家出走之後真的活下去。田村卡夫卡非常自律,你很難想像一個15歲的少年離家出走,是不停要鍛鍊自己。這是為什麼我總在村上的小說裡找到一個少年的影子是村上的影子,村上長年寫作小說的工作是極規律的,好像在青年時期就已經意識到,如果要在活下來的世界裡生存下去的話,必須要有怎樣的修行。
.
《沒有色彩的多崎作》這本書其實也有類似的共同性。主角多崎作在高中時認識了一群朋友,這群朋友的名字都有顏色,只有他沒有,所以他好像是透明的人。這個小說很有意思,他用一個成年的多崎作回顧他在青少年時期一個集體性極為強烈的時代,他怎麼在這個時期裡重新找到屬於他自己的顏色。
.
無論是田村卡夫卡或多崎作,村上小說裡的青少年們,在某種程度上所有人都在集體性往上的時代裡,他嘗試把自己擦拭得非常淡,這種淡是用強烈的自律性得來。在小說裡主角聽爵士樂、吃義大利麵,很多人會說這非常小資,可是我一直都覺得村上的人物會做這樣的行為,而且是重複、反覆的在多本小說裡做這些事情,是一種日常生活的反覆練習或是規律形成他自己的秩序,這個秩序感是他筆下的青少年或青少女,我覺得相當有趣的地方。
.
村上的音樂跟自我共鳴
✦欣倫:
我真的很喜歡村上春樹。《爵士群像》這本書很特別,除了由村上介紹爵士樂的樂手,跟繪者和田誠做搭配外,當時時報還跟唱片公司出一張收錄爵士樂手的曲目,而且應該是第一版,還有很多雜訊,真的很有時代的氛圍,很感謝時報出了這樣的書,讓我們在讀村上的時候可以去找裡面的音樂。
.
《村上收音機》則是一個短的專欄,很適合睡前看幾篇,但可能會停不下來很像吃洋芋片,因為真的非常的有趣。其中有一篇講一首老歌〈像在談戀愛的人一樣〉(Like Someone in Love),他說,最適合談戀愛的年齡是從16歲到21歲,如果再小就有點像小鬼頭不太用心,再大一點現實的複雜因素就會糾纏進來,年紀增加也會有多餘的智慧,不適合談戀愛。請大家回想一下,自己16歲到21歲的時候,是不是像他說的,應該勇敢又勤奮的努力談戀愛,因為這個時候是最單純的,不只是戀愛,像這種情感記憶的東西,就像是活生生水嫩嫩的原風景,即使年齡很大的時候,就會像一個不會熄滅的火星一直支撐你,讓你覺得這個世界曾經有那麼單純美好的一面,我們可能會覺得有點傻或是有點太天真,可他覺得每一個人這個時期都應該有這個火星,才能夠讓自己即使老了,或變得很無聊了,還是有個東西在支撐你。
.
不管是哪裡,只要能找到的那個地方
✧叔夏:
村上有一種獨特的幽默感,他其實表現在他某些小說創作,一些結構性比較沒有那麼的作品裡 ,比方說像《東京奇譚》這本書。這本是我個人還蠻喜歡的短篇小說集。這時期村上的短篇小說有一種簡潔,不像他早期《聽風的歌》那樣漂浮,可是又同時找到小說家在寫小說的那個零件。他的《東京奇譚》就充滿著這個零件的展示。村上以前的抽象小說都是有點象徵和童話的意味,但是到了最近這幾本小說的寫作,他好像嘗試在把握一種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所遭遇到的種種災難,這個絕對性裡面的偶然,在這偶然性裡面,他找到像神一樣的東西。很多人說他小說裡面是空虛,甚麼都沒有的,但我隱約覺得他小說裡有一種類似像救贖的事物,被隱藏在非常、非常後退的地方。
.
✦欣倫
村上春樹的小說,像《萊欣頓的幽靈》或《人造衛星情人》或是叔夏提到的《東京奇譚》,他都會寫到另一個異空間──他們可能去了「那裡」,如果熟悉村上的人就會知道,旁邊都要加個黑點點。《東京奇譚記》其中有一篇看起來像偵探小說,有一個婦人有一天早上煎蛋餅的時候,她的先生說要找他父母親,就去樓上,可是一直沒有下來,這個男人就消失了,所以偵探在兩個樓層之間一直徘徊找任何的蛛絲馬跡,問了經過的人,大家都沒有看到,後來一段時間之後,男人被人發現在某個小車站看起來有點像流浪漢,可是也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
我自己在讀的時候,覺得村上寫出了我們在寫實生活當中,有時候真的想要去一個某個地方,或是消失起來的那種感覺。不管是很擁擠的人際關係和虛偽的互動當中,或是你對日常生活已經覺得俗不可耐、重覆的這種過程當中,有時候我們就希望牆上有個洞,我們就可以去到另個地方一樣。《人造衛星情人》裡面的小堇、《萊欣頓的幽靈》那個充滿幽靈的空間、《東京奇譚記》消失在四十一層樓和四十二層樓中間的男子,還有《海邊的卡夫卡》中的歷史事件,十六個學生集體昏倒,身體雖然還在現實的場域當中,可是魂魄或精神性的東西整個消失了,集體的消失,我覺得這邊也有他的隱喻,少年少女在成人世界當中,有時候在面對沒有辦法處理的糾結的現實的時候,好像我們都要被集體催眠一樣,或是牆上希望有一個洞,讓他們到另外一個接受他們,或是比較舒適的空間。
.
.
.
走讀村上的東京地景
✧叔夏:
我自己在2010年第一次去東京,是一個人去的,因為那個時候我還在念研究所,是貧窮的學生時代,只是想要自己去旅行而已,買了廉價航空的機票,一個人就到了東京,但是到東京也不知道要幹什麼。我住的旅館,其實是在市中心以外的邊郊地方,這個旅館房間非常小,只有一張單人床,一個小桌燈,床尾一台電視,我就在這邊住了大概半個月的時間。每天早上,因為住在同間旅的背包客很早就出門去拜訪他的景點,所以我就在大家全部都出門之後,一個人去旅館的澡堂泡著,然後心裡想說等一下要幹嘛,大概是這樣子。
.
路上的街景很不觀光客,非常日常,你走在路上,你會發現到其實東京在那種大家常去的地方以外的住宅區,其實非常安靜,而且安靜到讓人覺得有點恐怖。我是夏天去的,夏天的東京天氣非常好,天空很藍,你走在其實一個人都沒有人的路上,你只看到公寓的陽台外面曬著他們的衣服,那些衣服在風裡飄飄飄,可是城市怎麼安靜到一點聲音都沒有。
.
因為這地方離村上在他的書裡常常寫到的都殿,荒川線的電車非常的近,所以我有好多天都是從旅館出門,我就走路到荒川線搭電車,買一日券的票,從早上開始搭,每一站都下去,電車終點是早稻田,它是從三之輪橋開到早稻田,我的旅館就在三輪橋。早稻田大學是村上春樹的大學,所以我有一天搭了電車到早稻田大學去,然後天真以為可以在那邊找到跟小說有關的蛛絲馬跡,我記得我用破爛的日文問學生說,請問一下你們學校有個宿舍(就是《挪威的森林》裡面寫的那個宿舍)可能是長什麼樣,結果他說學校裡並沒有這樣一個地方。但是電車沿途經過的許多景點,都是小說當中出現的,包括大塚站下車之後,這是他們夏日的祭典和附近的街景,這個畫面我後來在侯孝賢電影《咖啡時光》裡面看到,其實我覺得《咖啡時光》也是一個非常村上春樹的電影。
.
在這個旅程裡面我遇到的一個房子,剛剛欣倫分享《遇見百分之百的女孩》,裡面有一篇〈起司蛋糕形的我的貧窮〉,村上念大學的時候就和他太太結婚了,結婚之後,和他的岳父借了一筆錢以及向銀行貸款,在國分寺開了一家爵士酒吧,那個時候他們都很窮,所以這個〈起司蛋糕形的我的貧窮〉裡面寫到說,他們有次去找房子,東京有相當多在鐵路旁邊的房子,他們租到的房子是兩條電車的鐵軌交會,房子就在交會地帶的三角形。東京的電車班次很頻繁的,所以它從早到晚你會整天聽到電車跑,他寫,這條線有電車跑過去之後,沒多久又有另外一條電車跑過來,整天沒有安靜的時候,一直要到晚班車收班,他們才有一段安靜的時光。
.
「四月裡,照例有幾天是鐵路罷工的時候,一到罷工,我們真是幸福。電車連一輛也不在軌道上跑。我和她抱著貓走下鐵軌曬太陽,簡直像坐在湖底一樣安靜,我們正年輕才新婚,而陽光又免費。到今天我聽到貧窮這兩個字,就會想到三角形細長的土地,現在那個房子裡不知道住著什麼樣的人。」
.
我讀到這篇作品的時候,我很深刻感受到,他的小說為什麼之所以到現在還令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感到著迷,就是在那個你什麼都沒有的時期裡面,可是你們年輕、新婚、陽光又免費,一切世界正在為你而開展,我覺得這個是村上之所以可以在每一代十幾、二十歲的讀者裡面,重新又找到一個新的讀者的原因。
.